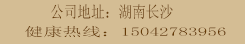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松鼠 > 松鼠的形状 > 人物陈国富监制少年班和他的电影资本论
当前位置: 松鼠 > 松鼠的形状 > 人物陈国富监制少年班和他的电影资本论

![]() 当前位置: 松鼠 > 松鼠的形状 > 人物陈国富监制少年班和他的电影资本论
当前位置: 松鼠 > 松鼠的形状 > 人物陈国富监制少年班和他的电影资本论
一、陈国富和《少年班》
作为一名电影人,陈国富的经验很丰富,身份也很多元。早年间他写影评做杂志,为杨德昌改剧本,干的是码字的活儿;后来他当导演拍电影,从文青必看的《征婚启事》到类型化的惊悚片《双瞳》,练的是镜头上的功夫;再后来,他又去哥伦比亚、华谊兄弟这样的大公司里做了“高层管理员”,开始在更宏观的维度上运筹帷幄。
对于如今的陈国富,电影圈里的人都习惯将他定义成“金牌监制”,从《非诚勿扰》到《画皮2》,从《狄仁杰》到《鬼吹灯》,陈国富监制的作品名头都很响亮。他辅佐过冯小刚、徐克,也提携过乌尔善和冯德伦,这一次,他又把一个他认为才华横溢的新导演带到了观众面前,这个新导演叫肖洋,他的电影叫《少年班》。
陈国富跟肖洋认识了很多年,为他监制一部电影却还是第一次。在采访这俩人的时候,他们都提到了肖洋剪辑《非诚勿扰》的经历,陈国富的说法是,他问肖洋敢不敢,肖洋说你敢我就敢。肖洋的说法是,陈国富问他敢不敢剪,并且说你要敢剪我就敢让你剪。两个说法有一点点出入,但结论就是:这两个人都很敢。
每一次问到陈国富所谓的监制经验,他都会从初心讲起,强调直觉,暂时性地回避后果。他认为,一部电影的商业与否,也都取决于结果的判断,而非意图或野心。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把做电影当成一场赌局,下注的时候全凭自己的先验性判断。他自己也说,在这个大数据横行的年代,这样做可能是有点不合时宜了。不过现在的陈国富依然很坚定,面对与互联网对电影产业带来的种种动荡,他说,真正懂得做电影的人是不为所动的。
陈国富做监制的时候,一直保持着一种兼容并包的姿态,他可以掌控几个亿投资的大阵仗,也可以去推动一些小成本的艺术性尝试。很多人会以为,他这是一手在精算市场,另一手在坚守这个台湾导演的文艺追求,但陈国富自己却不这么认为。他说,大有大做,小有小做,从心态上来讲,做电影是不应该有分别心的。就像这回他做的《少年班》,别人认为它卖相不好,他却认为自己的片子是“最具商业性”的,他说商业不是一种意图,而是一个结果,根本就不是创作者说了算的事儿。
二、对话陈国富
记者:什么时候注意了到肖洋这个人和他的故事?
陈国富:我就让他剪了一个预告,我也没见过这个人,剪完了以后约他见面,我就问他说如果我让你剪冯小刚的电影你敢不敢?他说你敢我就敢。我们俩是这么认识的,其实在那之前他也没剪过什么长片。
记者:后来他跟您聊到他自己的这段经历,才想把《少年班》拍成电影吗?
陈国富:对,我跟他聊到这个话题是他在帮我剪《风声》的时候,有时候停下来休息会聊聊天,我问他那个求学经历,他说他是上少年班的。我说什么是少年班?我没听过。他就跟我解释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很怪,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他就一脸纠结的表情。对他来说那个不是特别愉快的经历,我感觉。后来他想当导演,拍戏。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拍少年班?他说那有什么好拍的?我说如果我有兴趣,表示会有很多人有兴趣。就这么开始的。
记者:您觉得《少年班》算是怎样的一部电影?
陈国富:它还是一个青春片吧,青春成长片。当然我提《少年班》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会往什么方向去,我只是很本能的对这样的题材感到好奇,我会想看,我们总是对天才充满好奇,是一种奇观,电影就是要各种奇观。后来他写了几个人物给我看,就是现在我们电影里看到的这个方厚政、王大法、麦克、吴未,还有周知庸老师,他把这几个人物给写出来了以后,我就很确定这里头是有一部电影的。因为我一直在试不同的东西,所以我去试一个不一样的题材或者是不赶时髦是很正常的,我一直拍摄电影的经历里就没有这种一窝蜂的情况。对我来说不奇怪,我愿意跟任何人打赌,它是同档期里面最商业的电影。
记者:那它的商业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陈国富:就是我刚才说的,就说如果有一个题材我会那么好奇得想要去看它被实现,那一定有很大的群体跟我的想法一样,因为我是一个标准很高的观众,我一年进去电影院不到几回,如果能过我这一关,那应该就可以过很多人那一关吧。这不就是商业吗?因为商业不是一个意图,而是一个结果,就是有人去看了,很多人去看了,电影回收了甚至是盈利了,那就是商业。商业不是说我想拍个商业片,它出来结果就是商业的。
记者:您监制过《狄仁杰》、《鬼吹灯》这样的大制作,也监制过《转山》、《星空》这样的小成本,做这两件事的时候心态有什么不同?
陈国富:我说这个话可能很多同行会不太相信,但是我选择一个题材的时候我是不太考虑后果的,我的标准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标准。就算是《转山》也好或者《星空》也好,这么多年了还会有人提起来跟我讨论,说明它不是一个失败的作品,它是一个被人记住的作品。所以那就是我唯一的标准,我就是想做那种能留下来的东西。有些能留下来的东西当时特别受欢迎,有些可能要事隔多年才能被欣赏,但是这个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所以我的心情都很接近,就是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电影,或者是什么题材的电影,我一定要怀有很高的热情,因为你从一个电影的发想到去实现,最后还要去推广,过程很漫长,很辛苦,付出的精力您常常都觉得是拿生命在跟它的拼搏。如果你是怀着一点点功利的那个目的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干起来很辛苦的,你可能还不如去卖东西吧我觉得,去推销保险或者什么的,你回家就不用再担心那个事情了,我今天能做多少业绩,我今天回家我就彻底休息。但是干我们这行不是的,你是24小时,有时候你做梦还在梦那个镜头有没有拍好,周期有没有完成等等、等等的,所以我只相信那个声音吧。
深耕内地市场十余年,陈国富算是见证了中国电影市场化的每一步进程。作为一个影评人出身的文学性电影创作者,陈国富说:利益的驱使算不上什么原罪,一窝蜂的流行词汇也大可以成为茶余饭后的主题。在互联网企业放肆叫嚣的时代,陈国富执拗地保持着一种文人气节,大致的态度就是——你们热热闹闹地去讨论吧,因为你们很茫然,所以总要找出一些主题去聊一聊,就算找不到什么正儿八经的出路,起码也能缓解一下自己的茫然。不得不说,这种我自岿然不动的姿态,真是帅爆了。
记者:现在都在讲大数据,您还这么凭直觉,算是有些任性吗?
陈国富:我确实是有点不合时宜,当然我也可以比较谦虚的说就是我没学会那些东西,我每次看到一个名词或者一个概念经常出现的时候,我也会去思考和反省,就是我是不是没有与时俱进。但是我不知道,可能我自己就是一个大数据吧我觉得,就是我积累了一些经验,我看过很多的电影,从事过很多不同的电影工作,我做了不计其数的尝试,有些是成功的,有些不是那么成功的,这些就会在我身上积累出某种数据的概念吧。而且这个行业就是有很高的赌性,你说哪有一部电影是经过精密计算以后就保证成功的,我不太信那个。
记者:那您的工作有没有受到互联网的影响?
陈国富:我个人受到互联网的影响是一定的,因为我现在都不看碟了,都是在网上看电影,所有电影的预告和宣传素材都是在网上看的,但是我看得不多,这就是对我具体生活的改变。而且它也会改变我对电影的品位,我的审美也会随着受一点影响。但是总归我们这个行业就是回来说故事,不管你一直在讨论说这个平台现在变得多厉害,电影的售票的概念,或者是影院屏幕数的增加,三四线城市的崛起等等的,不管怎么把这个元素弄得越来越复杂,这个计算越来越困难,但是你就是要回来,我们的故事就是回来说故事,你就是要说一个好故事,然后跟观众产生对流。那一下是在影院里发生的,真的不是在你事先的营销活动里发生的,营销活动可以把观众忽悠进去,但是你不能保证观众在电影院里面得到的是最饱满的、最精彩的经验,我们做得还是这个最根本的,这个是多年来没有改变的,从电影发明到现在这个事情没有改变,你就是要在电影院里面让观众惊奇,让观众感动、让观众欢笑、让观众有一丝的幸福感这个是没有变的。
记者:就像现在大家很喜欢说互联网颠覆电影,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了?
陈国富:那个都可以说,就是反正就是说、讨论,大家总要有一些话题在茶余饭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同行大部分时候不知道怎么干这个行业,没谱,他没谱的时候就要抓一些概念来总结、解释,然后一段时间里面就会有点一窝蜂的这样,因为懂得怎么干电影的人是不为所动的。
记者:在这几年您觉得内地市场有没有一些进步的地方?有没有一些还是很令人头疼的地方?
陈国富:都有吧。进步是一定有的,因为市场变大了以后,利益就驱动人去发挥他的创造力,这个是不变的法则,这个是很经济学的东西。不满足的地方就是要假以时日吧,什么东西都有一个过程,中国电影发展太快了,快到他让很多人很焦躁、很慌乱,老怕错过什么东西,但是这样的心情是拍不好电影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你每一个项目的孕育都是很长的时间,如果你老在一种这一台没抢到可能就做过了那种心情的话,你没有办法好好跟观众说故事。都正常吧,我对于这种由于市场的放大,由于利益的增加而导致大家的热情,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有时候人的那个动力、人的那个创造的动力、人的辛苦劳动的动力就来自于利益,我是挺坦然地接受这个发展的。
成为金牌监制之后,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跟他聊市场,谈经济,仿佛他身上商人气质的标签越来越明显了。但有些影迷还是期待他能在亲自做导演,拍一些像《征婚启事》那样的作品出来,而不是一味地给其他导演做嫁衣。而陈国富本人却一直在模糊这两个职位的概念,他觉得,不管你在字幕上挂一个什么头衔,做电影时的投入方式都是没有区别的。
记者:《少年班》这样一个电影,投资的体量在您的经历中算大的还是算小的?
陈国富:算是中等的,就是说它虽然不是一个站起来一溜超一线明星这样的电影,但是它要保证所有的技术含量、所有的故事、所有的表演的细节都要到位,这种到位你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还有很重要的是它要达到一个工业标准,这是所有我参与的项目里头保证一定要做到的。就是不管我是做《狄仁杰》或者是在做《鬼吹灯》,或者是做《少年班》,它都要达到这个标准。
记者:因为《少年班》是肖洋的第一部作品,之前您也说过,对待不同的导演在做电影的时候相处的模式是不一样的,对肖洋是怎么样的?
陈国富:我跟他是太有默契了,所以合作关系跟其他导演是很不一样的,倒不是因为他是不是新导演的关系,就是我跟他工作了那么多年,知根知底了,默契很高,沟通起来无障碍。有时候那个合作经验太愉快了,我都有一点觉得是不是我们会把这个事情搞砸了,因为你知道有时候要做出好东西需要一些矛盾的,需要有一些焦灼,需要有一些争执,但是我跟他没有,完全没有,所以对结果满意,而且对过程还是有愉快的,这个比较少见。
记者:您在面对这样一个新导演的时候,会不会为了他的前途而自己有些压力?
陈国富:我不管面对什么导演,我的压力都是存在的,因为我就是不太允许作品的结果是失败的,所以就会有压力,这是一种责任,当然也是一种荣誉感。我其实没有把他们当做新导演,在工作过程中这个因素不太会存在,反而他们会提醒我说这个方面我不太有经验,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可能拍过几部戏的导演就不好意思这么提了,不好意思提是他的损失不是我的损失,因为他的损失就是他可能碍于情面,就没有得到更多的经验。新导演这一方面是比较好的,因为他总是期待你不管给他各种养分,给他各种更有效率的方向。我也比较善于跟这样的心理素质的导演合作,不一定是新旧的关系,是因为他愿意开放他自己,只为了结果的美好。
记者:您会不会把监制当成自己的一个主要的职业来看?
陈国富:外界常常在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恰恰是一个我平常不思考的问题,就是事情来,我就被吸引了,有时候是因为情感因素,有时候是因为题材的关系,有时候是因为我想象那个结果特别令人兴奋,我就很忘我的投入了,我没有去算计说哪些是监制,哪些是我自己应该导演的,以及我未来应该怎么规划,我是有一点走一步算一步那的人吧,可能未来还是会继续保持这种步调吧。
三、陈国富的电影资本论
监制+导演模式激活了华谊兄弟的生产关系,解放了导演们的生产力,博纳和万达等影视公司均想如此复制,金牌监制陈国富已被电影生产流水线绑架,停不下来了。
监制这事儿就像和魔鬼交易
邓丽君躲在后台抽泣。
第一次上电视演出,却紧张得忘歌词了,还被剧场经理嘲笑,15岁的邓丽君简直要崩溃了。化妆师很安静。旁边一个抽烟的女人安慰她,看了她的掌纹,说,“你是老祖宗赏饭吃,将来你不仅会红遍中国,还会红遍东南亚。”这时候,剧场经理又匆匆走进来,说节目不够,演出还剩30秒,让邓丽君上场唱半首歌。
又惊又喜,邓丽君冲出化妆间,奔向舞台。镜头虽然没展现舞台上的她,但从后台能看到投射的璀璨灯光,听到台下观众的欢呼生。
这短暂而情绪起伏的五分钟,来自昔日岁月的惊鸿一瞥,是陈国富拍的35毫米短片《初登场》。年,受台湾金马影展《10+10》联合制作计划邀请,陈国富拍了这部暗含个人况味的私电影。为了还原年代的化妆间,他还自掏腰包投资百万元。
有怀旧,有初涉人世感,有好友陈玉勋导演客串,陈国富用短片写了献给一代人的情书。他今年54岁,是最早北上掘金的港台电影人,先后监制18部影片,累计40亿元票房;担任华谊兄弟电影公司总监制7年,业绩显赫;自《天下无贼》起,跟冯小刚合作至今,包括以其成名作《证婚启示》为灵感的《非诚勿扰I、II》、《集结号》、《唐山大地震》、今年底将上映的《》;提携了高群书、乌尔善、冯德伦等新导演;今年同时有《画皮2》、《太极1、2》等四部监制作品面世。
但陈国富感到疲倦了。“金牌监制”的成就背后有煎熬,超级商业大片的上亿票房带来了焦灼。处于艺术与商业两股力量汇集的电影工业交叉点上,陈国富游刃有余,又消耗过度。他穿针引线,用“监制+导演”模式激活了华谊的生产无关系,解放了导演们的生产力,但他自己却被电影生产流水线绑架了。透支感越来越严重。他想停下来了。
不幸的是,他停不下来。电影的商业机器在残酷运转,他身不由己。监制这事儿就像浮士德和魔鬼墨菲托签的交易,已经把自己想当导演的灵魂抵押了。他内心深处有个黑洞:“我不光是一个职业制片人,如果有一天我没有创作的灵感,其他这些对我都没有意义。”
五分钟的《初登场》,陈国富让自己喘了一口气。“五分钟是一个创作上的挑战。你只能说最神秘的事情,往你自己内心去挖掘……邓丽君人生短暂,并且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但是她又总结了我们这一代的成长过程。她好不容易上了电视,但是她却当场忘词……”
这五分钟,是陈国富从影30年的浓缩,对年代台湾新浪潮的怀念,对自己闯荡大陆7年的叹息。“一个成长中的少女,很容易没有自信,很容易受到挫折,很容易感觉这个世界对我们是有敌意的。但是我想告诉她,一切都没有问题,你有非常灿烂美好的未来。”
这个青春期的少女,是陈国富对电影和自己的隐喻。站在后台望向舞台,这一刻,他意气风发,又充满忧伤。
类似3D大片《阿凡达》,《太极1:从零开始》也被看成了热血青年反抗强拆的故事。它发生在清朝中叶,小农经济对抗蒸汽时代,一代太极宗师杨露禅,率村民抵御清兵及威猛机械怪兽“特洛伊1号”。大都场面像iPad游戏:《切水果》、《愤怒的小鸟》、《植物大战僵尸》……
如此搞怪的功夫电影,二部斥资2.2亿元,是华谊兄弟传媒集团争议最大的项目。连陈国富自己都觉得“太疯狂”。男主角不是功夫巨星李连杰,而是个没有表演经验的武术冠军,导演冯德伦只有小成本电影的拍摄经验。但陈国富坚持做大片。在华谊最后一次立项会上,他说,“怕什么,我陪你们赌,责任我来担”。
他后来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我现在已经回想不起来拍这部戏的过程中我到底清不清醒。从做这个项目开始,同行都是用担心和同情、害怕的眼光看我,觉得这个东西会完蛋。”在今年夏天的发布会上,他撂下狠话:“从来没有人在‘十一’档战胜过我。”9月27日,《太极1》全国上映,票房过亿,成为国庆档票房冠军。10月25日,《太极1》票房逼近1.5亿,华谊又趁热打铁推出《太极2:英雄崛起》IMAX版,并在11月初发行2D、3D版本。
陈国富还说,《太极3》马上会启动,所有在第一集没挣到的钱,都会从第三集里挣回来。10月19日,华谊发布今年第三季度财报,营业收入2.59亿元,同比增长71.72%,但净利润下滑25.67%,仅万元。其中《画皮2》、《太极1》分别贡献了.55万元和.33万元的投资收入。
“陈国富效应”熠熠发光。
转折点发生在年底。在冯小刚的建议下,王中军、王中磊邀请陈国富担任华谊兄弟电影公司总监制。当时华谊正处于困顿之中,其商业模式最大的风险是对冯小刚的单一依赖。而陈国富当过导演,又在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做了6年亚洲区制作总监(其间参与了《功夫》、《大腕》、《卧虎藏龙》等的开发与监督,并监制《20、30、40》、《天地英雄》、《可可西里》等),懂得电影的艺术制作规律和商品生产流程,是能打通产业任督两脉的人。
“大陆电影开始有监制制度,是从陈国富起的头”,冯小刚说。陈国富把自己称为“中国式监制”或“内地式监制”,以区别于好莱坞的总监制,像《乱世佳人》的传奇监制大卫-塞尔兹尼克,要管电影拍摄的大小事务。他对华谊最重要的价值是判断力。《集结号》是关于普通士兵的战争片,票房近2.6亿;《风声》作为首部华语谍战大片,票房2.3亿;徐克导演的大片《狄仁杰之通天帝国》,票房2.9亿……
神奇的慧眼识金和点石成金能力。套用网络流行语:“元芳,你怎么看?”陈国富的专业判断关系到一个项目的生死。周迅、陈坤出演《画皮2》的绑定条款是:“由陈国富出任监制。”当乌尔善听陈国富说,他没有精力监制《画皮2》时,霎时冒了一头冷汗。华谊兄弟电影公司总裁王中磊说:“陈国富给我最大的帮助是勇气和判断:当我做出一项决断要有人鼓励我执行它;当我有勇气做一件事,又需要足够信任的伙伴来帮我判断。”
作为港台北上的电影人,陈国富与徐克、吴宇森、陈可辛等不同。“徐克、吴宇森也做监制,但更像是老派的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而陈国富是在一家上市公司的平台上做事。”陆川工作宣传总监王丹说,“像华谊这种要规模化发展的影视企业,会特别需要陈国富这样的人才”。
几年来,他从港台引入优秀电影人才,搭建了华谊兄弟电影板块从制作、发行到营销链条的各个环节。有了“陈国富监制”,这个电影品质和商业价值的保证,年,华谊发布“H计划”(英文单次“希望”首字母),将与两岸三地知名导演、青年导演合作,并把电影产量从每年一部大片跃升至每年8-10部电影。王中磊说,“在监制护航下,华谊在立项的判断和执行上已经接近成熟了。”换句话说,陈国富更被深度绑架了。
其他影视公司愈加感受到被丛林猛兽追赶的恐慌,并深切意识到陈国富对这家中国最大的民营影视企业的价值。根据中国电影家协会的数据,年至年华谊票房过亿的影片数量,占整个中国电影市场总量的19%,仅次于国有背景而位居第一的中影集团。
没有一部好电影在制作时其乐融融
竞争对手伺机而动。年,博纳影业老板于冬和陈可辛、黄建新联合创办人人电影公司,声称每年投拍15部电影。但该公司仅出品一部《十月围城》,就成了明日黄花。年,博纳接纳默多克入股,成为其第二大股东。博纳影业制片部总监郑叶说,“集团上下都希望,以引入好莱坞标准的制片工业流程……不走全产业链路线,维罗只能被其他巨头吃掉!”
今年以26亿美元收购美国第二大院线AMC的万达集团,以每年投资10部影片的速度杀入制片业。在决定做上游之后,万达传言最想挖到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张艺谋,另一个就是陈国富。“我们对监制的价值有两种理解方式,一种是用一个人能给你带来多少票房;另一种是,当你想做成一件事情时,你有几个人选?”《画皮2》执行制片人陶昆对挖角事件如此反应。
陶昆还说,“开发一部电影的过程,就像是一艘在茫茫大海上寻找油田的船。过程中充满凶险,不是有钱就能搞定那么简单。”
“监制,你骨子里头是不是有一种特叛逆的东西?”今年9月的一个晚上,在北京望京的一个烧烤摊,陶昆问陈国富。周围停着福特GT、雪佛兰V8等跑车,这里是“SCC超跑俱乐部”飙车少年们经常聚会的地点,很多电影人也经常现身。陈国富和几名幕后成员,在烧烤摊上聊到深夜。他回答说,“也不是那么叛逆,我只是老对别人下的结论持有怀疑。”
以前陈国富对陶昆说过一句话,“没有一部好的电影在制作过程中是其乐融融的,一定是痛苦重重、煎熬不已、斗争不断的,只求最后会出来一个好东西。”陶昆当时在别的公司,心想,“真严厉啊,他是在说我们拍戏的气氛太轻松”。
那天晚上,他们讨论了任正非的“狼性文化”,还说起了乔布斯的“现实扭曲立场”理论。这几个雄心勃勃的电影人认为,一个产业要不断往前走,是基于他的商业模式和创新机制……结论是,在中小成本的电影中创新,确立工艺流程,把相关经验用到大制作的商业片中。
见证了台湾电影从辉煌走向式微的全过程,陈国富总结为一道选择题:“是会计师在拍电影,还是创作人在拍电影?”他提醒道,“如果你迷信所谓的游戏规则,结果就是会计师在拍电影。那你可以看到尽头了,没有意外的结果,观众没有惊喜,票房也不会有惊喜。”同样,陈国富和华谊的模式是不可复制的。“监制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要看经验,但更要看每一部作品的即兴力量和创造发挥。如果把这种模式套用成公式那就算走到头了。”
如果说没在深夜痛苦的人不足以谈人生,没在黑暗中孤独过的人也许很难真正理解电影。陈国富是电影圈的异类,少交际,不喝酒,习惯待在暗处。他小时候喜欢躲在家中的壁柜里玩,后来喜欢观众进到电影院里大气不能喘的感觉。“很多同行把自己当业内人士、当专业人士、装成很理解电影生态的人,但我经常把自己当普通观众,看什么会打动我,会吸引我的注意,看你制作出来的产品跟我有没有关系”,他顿了顿说,“本质上,我还是一个影迷。”
没欲望前,摄像机不该启动
当初以影评人的身份进入电影业,经历了台湾电影的风云际会,陈国富问过侯孝贤,我们小时候看的都是通俗电影,虽然他是看了艺术电影才知道这个世界有多么宽广,但他毕竟还是看《小飞龙》、李小龙、张彻才迷上电影的。“当你手上终于握有资源和工具以后,怎么能完全背弃主流观众呢?”
任何行业起伏都要看回本质。陈国富不想做闷死大众的电影。“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好故事。”我的律条就是有没有尽全力,敢不敢相信自己的直觉,能不能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一秒钟,我觉不觉得没有把电影做好是一种耻辱。”
电影行业的“变态”在于,它往往是妥协的产物。导演与投资人、艺术与商业、演员与市场之间不断的张力,构成了电影的火光和遗憾。监制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他得调和投资方、出品方、导演、营销、院线的多方意志,在对抗中找到平衡。
青春残酷游戏。自己做过导演、监制,陈国富体验了很多阴暗面。
年拍摄《双瞳》时,有一次拍了14个小时,只完成三个镜头。他用近乎残忍的理性,压抑自己,冰冻他人。男主角梁家辉一度需要心理治疗,在电影首映后大哭。扮演小女孩的演员被CUT次数太多,流着眼泪委屈地说“不拍了”。这一切,陈国富浑然不觉,直到看拍摄花絮才了解。他说,“没有办法调节。最多晚上回家打开电视机,调成静音。”
这部投资近1亿元新台币的大制作,刷新了年台湾票房纪录,也影响了两个新锐导演戴立忍、魏德圣,两人在片中分别是演员、副导演,后来分别获金马奖最佳导演(年,《不能没有你》)、最佳影片(年,《赛德克-巴莱》)。
相比在片场统帅上百号人马,陈国富做起电影监制来更得心应手。他认为导演才是赋予一步电影风格的人,“在没有欲望之前,摄像机不该启动”。《双瞳》之后,他再没执导筒,心甘情愿为他人做嫁衣。
今年8月,《太极》在曼谷做后期制作。工作间像个超豪华家庭影院,漆黑一团,只有正前方银幕播放《太极》样片的光影,耳边传来震耳欲聋的电影原声。导演冯德伦和混音师完成了上百个轨道的声音效果。这一天,他们要接受陈国富的“检验”。每看完一段十来分钟的样片,陈国富就会从椅子上站起来,拿着写下许多建议的纸片,走到混音师旁边,用流利的英文交流。这间光线黯淡的小屋如同一个隐秘的洞穴,把焦虑暂时隔离,让他获得了片刻宁静。
深夜11点,他们从音效棚转移到另一个工作间,做最后的冲刺:海报的字体、颜色不断修改;预告片改出了20版,光河南话配音演员就找了10个人选;意大利文字幕也已翻译,为远赴威尼斯电影节做准备……凌晨2点,陈国富发现演员的面部画面还有些瑕疵,离开时嘱咐修片师,“要坚持到最后一秒”。
几乎就在同时,陈国富还遥控着其他几个分战场:当天北京有一场《太极》发布会,现场素材等他过目;微电影《伦敦魅影》第二集的脚本需要确认;徐克导演的下一部戏《狄仁杰前传》剧本尚待完善……
“电影拍摄涉及很多合作方,局面乱糟糟,意见太多,没有实质性的推进。”华谊市场部总监杨君说。有一年,陈国富把华谊的营销团队带到长城脚下的公社,用一天的时间讨论如何屏蔽杂音,为创意负责。“他是我们的定海神针。你不用说服那么多人,陈导能平衡各方的意见。只要你能提供好的建议,他就能帮你贯彻到底。”她补充说,但一定要有好的创意,“你糊弄,他一眼识穿你。”
《太极》出奇制胜:他们包下整个国贸地铁站,在上映前8个月做地面宣传;与凡客合作,推出“蒸汽朋克”涂鸦T恤;还借着伦敦奥运会的人气,花费重金制作微电影《伦敦魅影》。在来曼谷之前,陈国富彩排了首场发布会。那天晚上,他又细心地发现电影海报有一处褶皱。
演下去,直到穿帮
恨陈国富的人与爱他的人一样多。新生代导演们视他为心理医生、技术顾问和精神导师。《太极》拍摄时间长达一年半,冯德伦经常每天给陈国富打45分钟电话求教。《转山》导演杜家毅说,“他又能聊又能干,还能指导,这就要了命了!”老牌导演们反抗、漠视他,认为监制损害了导演的尊严和对作品的掌控权。高群书公开说,《风声》上映的版本,不是我的是陈国富的。”陆川助理说,“哪个导演愿意找来一个凌驾于自己之上?”
但陈国富不予理睬,他知道时代潮流在他这边。在中国电影的商业化进程中,他宣告:新一代主流电影作者诞生了。“新一代导演的优势是可以把自己放下,很愿意集思广益,向各种有经验的人讨教,搬救兵。这并不损及导演作为电影作者的思路。过去中国导演把无差别坚持自己的意见当作树立权威的方式,是把两件不同的事情搞混了。”
关键的问题,不是2D与3D的差异,不是好莱坞进口大片对华语电影的冲击该如何应对,不是电影审查制度,而是新一代主流电影作者带来的新的“电影资本论”:新的生产关系解放新的生产力。以前华谊尝试过签约导演制,与路学长、姜文、陆川等导演合作,但往往止于一部作品。王中磊说,“导演与投资方之间,如果没有沟通和妥协就难以合作”。“陈国富监制”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切。
入戏越深,灵魂越不安。冯小刚问陈国富,“你自己到底拍不拍?”他说,“我要拍。”他希望很快,他想拍关于人性深处的东西。几年前,他给王中磊写邮件,问自己的角色是当好导演,还是当好项目监制,还是整体团队规划?后者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带团队。
陈国富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希望年自己能减量,专注于一两个项目,更偏重个人价值而不是平台利益。但也许只是希望而已。在华谊的娱乐圈产业链里,他仍然是核心的重量级武器。王中磊在发布半年财报时说,“华谊的发展更趋于一家综合性公司,电影收入所带来的业绩、比例正逐渐见效,但电影是华谊标志性的品牌,电影带给我们的绝不仅是财报上的数字。”
他又在纠结。“我不是一个真正的制片人,也不太懂行业的基本运作,不太有兴趣经营公司或人事管理。我之所以进入电影的策划开发或营销,都是为了让一个作品准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我不能光拍或是光写剧本,我就逼着自己成为一个能够更多元地去影响这个行业的人,就要把上下的链条抓住……但是终究我的源头是电影,如果我失去了想象,我就什么都不是。”
这多像浮士德式的忏悔。“我最怕别人问我,监制应该做些什么?也许我就应该放弃质疑自己,凭我的直觉继续走下去,直到有一天彻底穿帮为止。”
只有那五分钟的邓丽君短片,和一张黑白合影照片(侯孝贤、杨德昌、吴念真、詹宏志),把陈国富最初的电影快乐保存了下来。后来,在法国导演、《电影手册》编辑、张曼玉前夫奥利维耶-阿萨亚斯拍的纪录片《侯孝贤画像》里,陈国富幽幽地说,“我愿意拿任何东西来换回那段岁月的经验”。
8月29日凌晨,威尼斯影展,《太极》的首映式即将开始。争奇斗艳的女明星、西装革履的男演员、时装设计师、娱乐记者们都在等待这场午夜电影。天上飘着细雨,一个清瘦的身影从侧门走出来。陈国富一言不发地走在街上,他从来没有在作品上映后再看一遍的习惯,“因为看到的只会是蔓延的遗憾”。他远离喧嚣,坐渡轮回酒店。他想起二十多年前和侯孝贤第一次参加法国南特电影节,路过威尼斯的情形:他们在地摊上买廉价围巾,准备戴着上台颁奖,在说笑中走过红灯区,目睹了毒品交易……那些回忆想想都浪漫。
本篇内容摘自《商业周刊/中文版》、电影网
(转载请注明出处)
转载请注明:http://www.songshuf.com/yldl/74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