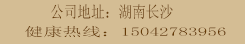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松鼠 > 松鼠的繁衍 > ldquo窗外仍有邻人哭泣rdqu
当前位置: 松鼠 > 松鼠的繁衍 > ldquo窗外仍有邻人哭泣rdqu

![]() 当前位置: 松鼠 > 松鼠的繁衍 > ldquo窗外仍有邻人哭泣rdqu
当前位置: 松鼠 > 松鼠的繁衍 > ldquo窗外仍有邻人哭泣rdqu
年《三联生活周刊》
杂志征订开始啦!(共52期)
点击上图立减元
文
刘怡
“老话题”过时了吗?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被陌生人提出关于终极价值的问题,尤其是在刚刚结束11个小时的经济舱飞行之后。不过假使面前这个陌生人有权力决定你的旅程是否可以继续,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今年10月的一个清晨,我就面临着这样一场不大不小的考验。在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的入境处,年轻的以色列安全官带着戒备的眼神翻完了我的整本护照,事无巨细地打听了我在过去三年里反复踏足一系列“非正常”国家——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等目的,随后一脸困惑地问道:“我理解你是个记者,但这些地方对一个正常人来说依然太危险了。有什么非去不可的理由吗?”我不清楚最终是哪句回答说服安全官给予了我进入以色列的许可,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次以色列—巴勒斯坦之行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鲜活的例证,足够说明国际观察者反复前往现场的必要性。在启程之前两个星期,我曾在北京与舍米·佩雷斯先生匆匆一晤:他是已故的以色列前总统西蒙·佩雷斯的小儿子,也是上世纪90年代一系列巴以和平进程的见证者。舍米对我回顾了他父亲生前的信念:给予巴勒斯坦人以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允许他们在一种非对抗环境下发展自己的社会经济,将有助于缩小巴(阿)以两个民族在收入方面的差距,进而为双方实现和解奠定基础。这是一种在20多年前颇为流行的观念,听上去也相当具有说服力。巴勒斯坦西岸:10月,在耶稣的出生地、约旦河西岸城市伯利恒,一道隔离墙将这座巴勒斯坦小城和以色列控制下的耶路撒冷划分成了两个世界。但它和现实未免相去太远了。在我真正进入属于巴勒斯坦国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并与一位年轻的阿拉伯大学生一同拜谒过阿拉法特墓、卡兰迪亚检查站乃至西岸隔离墙之后,由衷的怀疑渐渐浮现出来:今天的巴勒斯坦已经得到了形式上的独立以及相当可观的经济增长率,但它的国民并不会因此感谢以色列政府的“恩赐”。无论是盘踞在西岸领土上的犹太人定居点和检查站,还是带有殖民色彩的经济控制以及围墙隔离,都阻碍了一个真正健康的巴勒斯坦公民社会的出现。那些渴望获得个体尊严和自由迁徙权利的当地年轻人,所欲求取的早已不再是20多年前由佩雷斯和拉宾定义的那种“和平”;世界的变化,同样渗透进了巴勒斯坦。我的这篇以《约旦河西岸的生与死》为标题的观察记,刊登在今年第48期《三联生活周刊》上。就像过去几年中我曾经反复记录和评论的阿富汗现状、叙利亚内战、南海博弈一样,巴以冲突是一个“老”话题,是一个曾经在某些时段被渲染得人尽皆知、以至于大众对它们已经产生了信息疲劳的“过时”话题。但“老话题”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对它们的了解就足够充分——事实上,由于专业人才的匮乏和工作模式的落后,中国媒体从全球冲突最激烈的前沿发回第一手报道的能力极其羸弱。所谓的“信息疲劳”,在许多时候仅仅意味着舆论场内充斥着各种质量良莠不齐、来源真假难辨的二手、三手材料;基于这些低质量信息形成的对世界事务的理解,不仅狭隘,而且偏颇。于是便出现了极其怪异的反差:一方面,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公民旅行、迁徙的范围已经延伸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另一方面,中国媒体自身能提供的优质国际报道数量却严重不足。这就是那个“非去不可的理由”:我们不能永远指望通过他人的视野去了解世界,更不能对良莠不齐的信息一概兼收。需要有一些人到现场去,到冲突最激烈、因之暴露的问题也最充分的前线去,到人性中的善和恶都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失败国家”去,留下关于这一切的真实记录。重返巴格达:2月底,在巴格达拉希德大街重逢三年前的采访对象、“回声”书店老板里亚德,把刊登有他故事的杂志赠送给他。当我从年7月开始参与周刊的国际报道时,怀抱的就是这样的志愿。我也曾经从一位伟大的前同行那里获得过指点——年4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亲口告诉我:“不是伟人的才智,而是每一个真实地生活过了的小人物的故事,结合起来才构成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应当让这些常常被忽略的小人物来叙述他们的经历,叙述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拼搏,叙述他们对那些伟大思想和伟大人物的看法。”这也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年《三联生活周刊》
杂志征订开始啦!(共52期)
点击上图立减元
邻人的哭声每一年,我都会碰到上百个宣称自己拥有战地记者梦想的年轻人——之所以称之为“梦想”,正是因为其中夹杂有太多浪漫化的想象。事实上,进入前线之后的报道工作依然充斥着一系列希望渺茫的尝试和焦躁的等待,还涉及评估预算、说服助理和司机、申请许可证等等种种琐碎细节。有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会吞噬掉你的出行预算和所有既定安排,有时一则真伪难辨的传闻就会让预约好的拜访对象打退堂鼓。浪漫是这份工作最不需要的特质,起作用的是稳定的心理素质、接受自己可能失败的准备,以及一点点运气的眷顾。今年元旦之前几个小时,我和搭档李亚楠经土耳其飞抵刚刚复航不久的大马士革国际机场,与叙利亚首都的民众们一起观看了内战爆发以来第一次新年烟花表演。随着中西部地区的战事接近尾声,大马士革东郊已经不再像我年初到时一般响彻迫击炮和火箭榴弹的啸叫,但距离真正的和平仍有迢迢万里。历时两个多星期的旅程中,我们进入到瓦砾遍地的北方名城阿勒颇、内战初期巷战作为激烈的逊尼派聚居区霍姆斯和哈马,努力穿越政府军设置的警戒线,拍摄下不为外界所知的真相。跨年之夜,大马士革多玛门广场上自拍的叙利亚民众。和某些自媒体伪造的假新闻不同,战火中的人们依然竭尽全力维持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摄影:李亚楠)回国过完春节之后,我们再度启程,进入此前中国媒体从未踏足的叙利亚东北部库尔德武装控制区。为了完成这次毫无把握的采访,我们首先飞到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转道那里北上伊拉克库区首府埃尔比勒。在办理好进入叙利亚库区的身份证明之后,又需要乘汽车穿越公里沙土路,通过设在底格里斯河上的边境口岸,才能到达代尔祖尔省的前线基地。在奥马尔油田附近的“绿村”媒体营,大约40名国际记者一起等待着那个重要时刻——对“伊斯兰国”最后控制区巴古兹镇的总攻开始,我和李亚楠是其中仅有的中国人。由于绿村和巴古兹前线之间大约公里的土地已经沦为无人区,我们必须在日出后的第一时间从基地出发,前往当天的主要目的地:可能是收容俘虏的现场,可能是某座被彻底摧毁的村庄,也可能是距离包围圈仅有5公里多、不时能听到机枪射击声的前沿阵地。罗贾瓦战地:3月初,和“绿村”的国际住户们同车前往巴古兹前线,报道对“伊斯兰国”的最后一战。由于电力设备已经遭受严重破坏,傍晚6时日落之后,四周将变得一片漆黑,我们也必须跟随库尔德士兵返回基地。运气好的话,食堂窗口会递出一份半温的西红柿茄子汤和一袋面饼;但大多数时候,除了干面饼和凉水以外就再无他物。这倒使整个兵营意外笼罩上了一股共产主义气息——在躺到脏兮兮的地铺上以前,记者们会围坐在篝火边,分享自己在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以及各种糟心地区的采访体验。这些与北京的日常生活距离甚远的经历,被我写入了今年第15期杂志的封面报道《寻路叙利亚》中。在那期报道里,我记录下了过去两年三次进入叙利亚的见闻:在历史超过年的古城阿勒颇,倭马亚清真寺的穹顶上残留着被炮弹击穿的大孔,阿加莎·克里斯蒂写作《东方快车谋杀案》的男爵旅馆已经门庭冷落。在“伊斯兰国”一度自称的“首都”拉卡,摩托车和骡马在沼泽一般的街道上穿行,市政委员会在一所废弃中学里办公,年事已高的母亲抽泣着向我讲述儿子被恐怖分子折磨致死的经过。霍姆斯老城的建筑废墟中,几名年轻人用卸下的窗框和门柱生火,煮了一大壶茶与我分享。战前这里曾是一间餐厅,如今则安静有如墓地。阿勒颇废墟:1月初,在阿勒颇新城的废墟中,一群叙利亚小女孩和我搭话。她们似乎还没有学会悲伤(摄影:李亚楠)在冲突和死亡发生的现场,仅仅矫情地喊出一声“和平可贵”是浅薄的。亲眼见证过这样的场景之后,你会去思考杀戮背后的深层机理,也会由衷生出对受难者的同理心。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他人的苦难中固然包含有某些“本土性”,但更多的是偶然性。未必是更高贵,也未必是更智慧:一些人可以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另一些人则必须时时与死亡、匮乏和恐惧为伍,完全可能是随机效应的结果。关心他人——那些正在窗外哭泣的邻人——的命运,间接构成对自身命运的观照,也构成人类作为一种智慧动物的道德属性。属于“常人”的视角过去的三年时间,我每年会乘飞机飞行大约10万公里,有时在4、5月份还要翻墙倒柜找出羊毛大衣,11月却又要带着一捆短袖T恤离开北京。为了在漫长的旅途中不至于无所事事,我会选择阅读前辈同行在许久之前写下的关于目的地的文字:今年春天反复进出叙利亚时,读的是前《纽约时报》贝鲁特站首席记者罗伯特·沃思(RobertF.Worth)三年前出版的报道集《渴求秩序:动荡中的中东,从解放广场到ISIS》。5月初拜会阿富汗前驻英大使瓦利·马苏德(他是传奇抗苏英雄“潘杰希尔雄狮”马苏德的弟弟)之前,重读了塞巴斯蒂安·荣格(SebastianJunger)在年对他哥哥的最后一次采访手记《雄狮在冬日》。11月前往尼日利亚途中,则又一次回味了25年前罗伯特·卡普兰(RobertD.Kaplan)关于非洲问题的名作《无政府将至》。叙利亚
新闻报道被认为是一种时效性特征显著的文体,且其叙事逻辑的展开相当依赖采访对象的口述,然而后者的可靠性恰恰很值得怀疑。我曾经在不止一次采访中发现,一个表达欲旺盛的采访对象会对他陈述的往事做出主观色彩浓厚的评判,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普通人也很难就过于宏大的话题提出有建设性的看法。
阿列克谢耶维奇告诉我,假使没有时间限制,通常她需要和每个受访对象聊5到7次,才能捕捉到对方的真实心理:这样的奢侈只有在极其罕见的场合下方能具备。因此,我会尝试在不依赖受访对象口述的情况下,利用其他更不易波动的素材建构属于自己的记录纵深。这些素材包括统计年鉴、政府公文、已经出版的研究著作和论文,乃至对于环境的直接观察——当地传统市场和新兴购物中心的物价状况,早晚高峰时的交通秩序,身着制服的司法和军事人员的出现频次,外汇是否容易兑换……惟其如此,我才有能力验证采访内容的可靠性。拉卡黑牢:3月初,拉卡,一名失去儿子的库尔德人母亲在曾经的“伊斯兰国”黑牢中流下了热泪(摄影:李亚楠)
前辈记者留下的记录,尤其构成一种有价值的参照。我会相当认真地复盘那些完成于10年或20年前的作品对未来的预测,尤其是其中已经被证明和真实历史截然不同的部分。他们是基于哪些依据或判断做出了那样的预测?出现偏差的是其中的哪些部分?这些偏差,是否也有可能干扰到了他们在当时对探访目的地的认知?这种不间断的追问,同时也构成一种智识趣味,使得新闻报道的价值不再仅限于提供短期信息。一名真正的记者同时也应当是具备足够研究能力和独立思考精神的知识分子,这一点在今天的世界尤其有意义。作为曾经的国际政治系学生,理论工具和历史案例依然是我分析世界问题时的重要透镜,但它们并不能完全替代观察和记录中的“常人”视角。尤其要警惕浅薄地滥用历史分析法,警惕过于“万能”的解释路径。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了提升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年我参与了两个不那么“传统”的国际话题的报道,它们是第23期的封面故事《全球产业链的微观调查》(越南篇),以及第49期的《非洲诱惑》(尼日利亚篇)。非洲诱惑
全球产业链的微观调查
越南与尼日利亚,就贸易数据而言与中国关联颇为密切,在普通中国人的认知中却早早被贴上了“贫穷”“混乱”“对中国人不友好”的刻板标签。我所记录的几代华人企业家在当地筚路蓝缕、艰辛创业的故事,既是向他们的开拓精神的致敬,也是全球变化在个体命运身上的投射:从上世纪60年代华人资本进军西非到国际贸易格局剧变之后的“抢滩”越南,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变化,影响到的则是每一个真实、具体的个人。
11月,在尼日利亚采访万通银行亚洲业务总经理张文海(摄影:李亚楠)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英国人墓园是我相当喜欢造访的一处目的地。它的建立最初是为了安葬死于~年第一次英阿战争的英军官兵,随后渐渐变成了所有去世在阿富汗的外国人的埋骨之所。在那里不仅安息着伟大的中亚考古学家斯坦因,还有近百位不那么著名的普通漂泊者:20世纪初前来寻找商机的美国推销员,在当地酒吧弹唱的白俄钢琴家,德国外交官夫妇夭折的婴儿……一位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和一位远嫁来此的西北妇女亦在其中。5月,重访喀布尔,在斯坦因的墓碑前留影。他们构成了那些属于“常人”的故事:没有那么多大国权谋和“历史必然性”,仅仅是每天都在发生的喜怒哀乐、生离死别,但依然构成将陌生的国家和不同属性的文明连结到一起的纽带。当邻人的哭泣声从窗外传来时,一个有责任心的记者没有理由对其视而不见。他应当去倾听,去理解,去记录。最后,分享一段我在年印象最深刻的经历吧,它发生在叙利亚古城阿勒颇的老城区。在那里,由于返乡难民为数尚少,一整个街区往往只有两三户人家存在住客。当我和李亚楠开始检视一辆被遗弃的汽车的残骸时,一阵婴儿的哭声从我身后的窗户里传了过来,响得格外真切。哭声持续了好几分钟,接着传来了一阵诙谐的音乐。音乐开始之后,哭声渐渐小了下去,最终变成了大笑。抬头望去,炊烟正从窗口徐徐冒出。那段音乐是大部分中国年轻人同样会熟悉的:它是米高梅经典动画片《猫和老鼠》的开场乐,伴着那一声几十年不变的狮子吼叫。即使是在这个星球上最残酷的角落,依然有《猫和老鼠》,生活依然在继续。作者档案
刘怡
周刊特约主笔,原《战争史研究》副主编,不擅长聊天、没有社交网络账号的文字工作者。
26分钟前
三联生活周刊
—END—年三联生活周刊点击图片,一键下单(赠送年故宫日历,期期快递)▼点击阅读原文,一键订阅(52期)。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转载请注明:http://www.songshuf.com/ylzz/56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