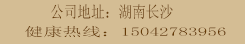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松鼠 > 松鼠的繁衍 > 一个中国记者眼中的以色列上
当前位置: 松鼠 > 松鼠的繁衍 > 一个中国记者眼中的以色列上

![]() 当前位置: 松鼠 > 松鼠的繁衍 > 一个中国记者眼中的以色列上
当前位置: 松鼠 > 松鼠的繁衍 > 一个中国记者眼中的以色列上
[这是我年10月访问以色列回来写的一篇通讯。当时,国人对以色列的了解不多,我们同行的5个记者中只有一个人曾经去过。以色列政府邀请中国记者去采访,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感受与介绍,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以色列。行前,以色列驻华大使专门与我们座谈,介绍了一些情况,但我们仍然是带着许多问号踏上旅途的。一周采访归来,我们对以色列有了很多感性认识,也有了一些理性思考……
12年过去了,年末,那里爆发了新的局部战争,以色列再次引起了人们的 我随中国记者代表团赴以之前,就有不止一个人叮嘱:注意安全。自己虽一笑置之,却也心存疑虑: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会看到什么景象?毕竟一周前刚刚开放枪禁,恰恰中东和谈前景扑朔迷离……
访以归来,许多问号释然了,我想应该告诉读者一个我看到的真实的以色列。
11月3日星期日晴宁静的耶路撒冷
飞机掠过夜色笼罩的地中海,抵近位于东岸的以色列第二大城市特拉维夫。从舷窗俯视,但见一片灯海。想想这座城市不到40万人口,不及中国的一个小城,竟如此繁华,不禁令人惊叹。
都说以色列入境检查极严,为的是防范恐怖活动。例行的询问包括“为什么要来以色列?”“谁邀请的?为什么邀请?”“到以色列谁来接待?费用谁付帐?”因为我们执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又是以色列政府邀请的客人,所以通关很顺利。
以色列外交部的娜法小姐来接机,司机是一位叫阿立克的小伙子。汽车驶出机场,沿国家一号公路去耶路撒冷。45分钟的路程,已经从沿海平原进入山区。
娜法说,我们的国家很小,实际控制面积只相当于中国的北京、天津两地之和,人口只及北京的一半。国土狭小,南北最长处公里,东西最宽处不过公里,最窄处只有15公里。从耶路撒冷继续东行一小时就可以出境了。有人说,在世界地图上,因为面积太小,“以色列”的国名只能印到地中海里去了。团长老许风趣地说:“你们国小名气大。中国古语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嘛。”众人大笑。
耶路撒冷意为“和平之城”,散落建在七座小山丘上。我们到达时已是夜晚,街头十分宁静,毫无城市的喧嚣,更无紧张的气氛。稀稀落落的行人,缓缓驶过的汽车,使我们相信这是一座平静的城市,尽可安然入梦。
11月4日星期一晴万幼小生灵
因为时差关系,很早就醒来了。打开窗帘,晨曦中的耶路撒冷呈现一片洁白的亮色。耶城建筑的显著特点就是一律以白色的石头作外墙,这是历史传统,就地取材,节省原料。如今有了钢筋水泥,建筑外墙依然敷以白石,因此,整座城市形成了统一的格调,很有特色。
按照日程,代表团首项活动就是游览耶路撒冷老城。在这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内,竟汇集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世界上三大宗教的圣地,堪称奇迹。也难怪各教信徒为此争端不已。老城街道上行走的人们,既有身着黑色服装极端正统的犹太教徒,也有穿着华丽的阿拉伯妇女,还有衣着色调暗淡长袍的基督教传教士,显示着这里的宗教汇集。
老城极好地保存了原貌,小巷中的店铺、人家,会使人想起国内的古老小镇。即使已经毁坏的历史遗迹也原样保存着,只是旁边附有原建筑的图示,告诉游客这座城市曾经有过的辉煌。据说,老城居民中,阿拉伯人占了多数。
早晨送来的报纸上说,有恐怖分子潜入中部地区,这使我们多少有些紧张。果然,耶路撒冷随处可见佩枪的青年男女。我们为之拍照,并无人制止。周围的人们司空见惯,我们很快也就处之泰然了。我问阿立克:“你也带枪么?”他顺手就从腰间拔出一支手枪来。娜法解释说,带枪是为了防范可能的袭击,除非是恐怖分子,没有人会胡来。
依次参观了耶路撒冷老城的各处古迹,在著名的“哭墙”前,我学着犹太人的做法,塞一张小纸条在墙缝里,祈愿中东和平,世界和平。
下午参观大屠杀纪念馆。馆前一片茂密的树林,每棵树前都有一块小小的铭牌,以纪念那些曾经在战争时期给避难的犹太人以帮助的正义者,其中就包括世人皆知的辛德勒先生。这样的纪念树共有多棵。如同人们知道的犹太民族在战后始终没有停止对于战争罪犯的追杀一样,犹太人民也没有忘记朋友,始终在寻找那些正义者,为他们树碑立传。
“二战”期间,有万犹太人被法西斯屠杀,成为这个民族历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纪念馆完全以黑色为基调,充分表现了民族的苦难,给人以沉重感。更为震撼人心的,是被残杀儿童纪念馆。前厅橱窗内一幅幅巨大的照片上,天真烂漫的孩子在向你微笑,而大厅内却一片黑暗。点点烛光被无数块玻璃折射出无数个亮点。黑暗代表着法西斯,亮点象征着生命,那是万个幼小生灵啊!空旷中传来低沉、缓慢的解说,周围有人在啜泣,参观者都沉浸在悲痛之中。这种纪念方式的感染力、震撼力,远比呆板的陈列、乏味的解说要强百倍。
今天恰逢以色列前总理拉宾遇刺一周年,我们前往悼念。拉宾墓地只占墓区一角,一段砂石路,一块黑墓碑,简朴、庄重。墓前摆满了鲜花、蜡烛,许多自发前来的人默默肃立,不时有人按习俗在墓碑上放一枚小石子,悼念这位为中东和平献身的政治家。
拉宾遇刺周年,以色列民众悼念
采访以色列议会,需要通过严格的安全检查。接待人员首先向我们介绍的,是议会大厅内展示犹太民族历史的巨幅壁画。采访第一天,我们几乎无时无处不在感受有关犹太人、有关以色列的历史。他们太重视、太珍惜自己的历史了,对客人更是不厌其详地介绍。我想,这恐怕正是这个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以色列,旁听议会辩论是公民的权力。旁听席设在二楼,约有个席位,而楼下的议员席却只有个。今天的议题是关于罪犯引渡问题,几位议员相继到台上发言,下面坐的议员很少,甚至不如旁听者来的多。后来到休息厅我才发现,大多数议员都在那里交换意见,确认彼此立场,表决时才会回去。这是我第一次领略西方式议会开会的场景。
采访左翼党(梅内兹集团)女议员诺米-海森,谈“土地换和平”问题。她明确表示反对现任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安全换和平”政策,并且逐一指出政府的失误,但她并不问我们的立场。在那里,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议员们在议会都有各自的办公室和必要的工作人员,每天要上班、开会,要研究、讨论问题,要接待公民来访,要处理许多庞杂的事务。做议员并不轻松。
11月5日星期二晴还有中共党史课
上午采访医院——医院。这里环境优雅,设备先进,医院的那种嘈杂、脏乱。全院名医生,张病床,医患比例居世界前列(以色列全国1.1%的人口是医生)。重要的是,医院招聘医生,要求不仅能诊治疾病,而且必须能搞科研,因此,他们拥有一批高素质的人才,并且在医疗技术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母婴中心的产房完全家庭化,连手术器械柜都是按照家具设计的。儿童病房更具温馨,充分考虑了孩子的生理、心理需要,连卧具、餐具、卫生袋、甚至一张衬纸都设计了儿童喜爱的图案,活动室还配备了电脑、玩具,对孩子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唯一的“防范”措施,是病房的大门把手距离地面约两米高,孩子够不到,就不会随意跑到外面去了。
以色列朋友说,人是最宝贵的资源,因此,对人,特别是孩子呵护备至。据介绍,只要参加了一定的保险,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到医院的治疗。
以色列政府鼓励人口生育,对孩子多的家庭,国家会给予补贴。阿立克已经有三个孩子,他还希望再生。他说,我们犹太人只有几百万,还需要更多的人口。
特色儿童病床
我们知道,现在的以色列人口中,有相当部分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移民。以色列政府根据什么允许他们加入以色列国籍呢?询问得知,一是确认母亲为犹太人的,二是确认皈依犹太教者。这第二条是不论民族和信仰的。因此可以说,今天的犹太人已经不是一个种族概念,而是一个宗教文化的共同体了。这种“四海一家”的“大犹太观”,对于犹太人和以色列在世界上展现的实力与影响,决不可小觑。
下午采访希伯来大学杜鲁门研究所。著名汉学家希霍尔教授的研究课题是“中国军工企业转产民品”问题,另一位学者帕姆研究的竟是中共党史中“薄一波等61人叛徒案平反”问题。我问:“为什么研究这些?”前者回答:“由于战后以巴冲突不断,以色列的经济实际上始终没有脱离战时状态。随着中东和平进程,转变成为可能,中国企业军转民的成功经验对我们有借鉴作用。”后者则在为东语系的多名学汉语的学生讲授中共党史。在这样一个只有万人口的国家,还有许多人学汉语,而且开设中共党史课,这是我无论如何想不到的。
再次到议会采访。今天见的是右翼党(利库德集团)议员希特里特。他为现任政府政策做了详尽的解释,也坚持了本党在对阿拉伯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主人这样安排采访,无非是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以色列,我们也在采访中多少领略了西方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微妙关系。
随后参观以色列博物馆。导游是一位老年志愿者,义务讲解,仍然是滔滔不绝地介绍犹太民族、宗教、历史。一个民族对自己的历史文化钟爱到如此程度,确实罕见。
与以色列外交部亚太司副司长谢勒夫共进晚餐。席间谈话,再次印证了上述感受。他说,由于犹太民族长期流散世界各地,希伯来文除了保留在犹太教祷告词中的少数词汇,已有0多年未能使用。以色列建国后,大力推行民族语言、文字,希伯来文成为国家法定公用文字,凡是以色列公民,无论你原来在哪个国家,用什么语言文字,一律改用希伯来文,连总统也不例外。但是,时代在发展,新事物层出不穷,希伯来文原有的词汇已经远远不够使用,不得不杂以许多外来词。因此,以色列的语言文字专家不断研究、挖掘、创新,几乎每月都由政府公布新词表,让公众学习、使用。看到以色列人为保持民族文化传统所做的能力,想到我们的生活中许多人不珍惜民族语言文字,以致出现异化、洋化的现象,真是汗颜。
11月6日星期三小雨总统退休搞科研
晨起离开耶路撒冷。天上飘落淅淅沥沥的小雨。中国有民谚“春雨贵如油”。在干旱少雨的以色列,可以说“逢雨即为油”。
以色列大部分国土是缺水干旱的沙漠和很难生长植物的荒山,离开花园般的城市不远,便不见了绿荫,路旁尽是砂石丘陵。因此,以色列人对绿化极为重视。建国之初,全国的树木不过万株,经过40多年坚持不懈的植树活动,已使这个数字变为两亿。在以色列,随意攀折花木是犯法的。许多人植树后,假日还专门驱车去看看成活与否、长势如何,做些浇水、修剪的工作。我们每年也种树,千军万马齐上阵,声势浩大,轰轰烈烈,但事后有多少人关心植树成果?
上午参观一所社区实验小学。让孩子从小就接触现代科学技术,掌握并运用先进工具,是他们搞实验的目的。在这所学校的教室里,没有通常所见、排列整齐的课桌椅,也没有黑板、讲台。整个教室分为三个区域,即剧场坐席式的授课区(使用电视、投影仪)、三五成群按兴趣围坐的活动区(面积最大)、室内二层的电脑操作区(用于完成作业等)。学生们每天三分之一的时间分组活动,而不必“挺直腰板手背后”,静坐听讲若干小时。在这样的条件下学习如同游戏,自然于身心大有裨益。
这所学校有一种独特的编班方法,除二年级有相对独立性以外,把学龄前儿童与一、三、四、五、六年级孩子混合编班。校长解释说,孩子的智力并不是严格按年龄划分的。交叉编班有助于发现人才,也考虑到孩子学习人际交往的需要。对于单科成绩突出的孩子,学校会请老师强化辅导,但一般不会让他“跳级”,同样是考虑孩子的社交能力。我们在国内常常谈论教育培养应试型还是能力型人才的问题,以色列的教育显然更注重后者。
以色列国土有限,资源匮乏,国内市场狭小,周边关系紧张,要生存与发展,必须寻找适合自己的途径。专注于高科技、着眼于全球化,成为以色列的必然选择。正如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本-古里安所说,对科学研究及其成果的追求,不仅仅是抽象的知识追求,更是关系民族存亡的关键因素。
以色列政府历来肯于把大笔资金投入教育、科研,谋求长远发展。他们说,我们一无所有,能够开发的只有国民的头脑。几十年的努力,使现在以色列每万人口中,就有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科学家、工程师,这个比例高居世界第一。
值得一提的是,年代以来,由于前苏联解体,约有百万人口涌入以色列。前苏联移民大部分是工程师、科学家、技术人员,据估测,他们给以色列带来的经济价值约亿美圆,等于苏联为以色列免费培养了一支科技大军。
著名的魏茨曼科学研究所,每年研究课题所需经费的60%来自政府,40%来自中介机构、大公司和私人捐助。研究所走科研和生产、贸易相结合的道路,能够把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和应用,尽快产生经济效益。注重应用技术的研究与推广,是以色列发展高科技的重要方面。
这家研究所出了两任国家总统,创始人魏茨曼先生便是以色列第一任总统。而第四任总统伊弗雷姆?卡齐尔是著名生物化学家,卸任后仍回到实验室继续他的研究。
这里的研究人员实行聘任制,长期没有科研成果的一律解聘。获得终身教授资格的条件极严,据说要会六种语言,要有著述,由专门委员会批准。在这里留学的中国研究生说,这里“人人头上一盘石”,许多人每天带几片面包、几根胡萝卜就钻进实验室,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
研究所规定,研究生中须有30%来自国外,为的是一方面扩大研究所的影响和知名度,一方面不断“引进”新思维,保持领先地位。以色列人确实精明。
今天的日程还包括访问为发展中国家培训人才的国际农业发展合作培训中心和特拉维夫大学战略问题研究所。夜宿特拉维夫地中海畔。但见高楼林立,灯火辉煌,小汽车如过江之鲫,完全大都市风貌,与耶路撒冷形成现代与历史的鲜明对比。
(未完,待续)
本文作者张刃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songshuf.com/ylzz/5805.html